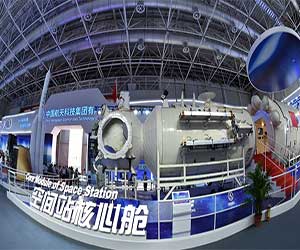怀念钱谷融,怀念光风霁月
近年来,常有一些学者的凋零,跨越了学科的界限,自发地引起整个社会的广泛关注。譬如之前的周有光、杨绛、傅璇琮、叶秀山、陆谷孙、童庆炳、李小文等,又譬如近日辞世的著名文学理论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钱谷融。
如果单纯以“著述等身”的标准来衡量钱先生,大约会有些难以理解为什么钱先生的离去,足以引发朋友圈无论行业无论年龄的集体悼念。但如果对钱先生的为人和履历稍有了解,不难得出答案。
新中国成立之后,文学尤其是文学理论前所未有地上升为国之显学,同时也被置身于时代的风口浪尖。钱谷融先生与他同时代的朋友徐中玉、蒋孔阳等人,成为上承朱光潜、黄药眠、周扬、冯雪峰等老一辈学人,下启钱中文、童庆炳、曾繁仁、朱立元等新时期学者的关键衔接。钱先生这一代人,大都受教育于解放前,在建国初期的历次运动中,自然也是步履艰难,命运坎坷。
钱谷融的命运同样不能另外。50年代因《论“文学是人学”》《“雷雨”人物谈》两次遭到大批判。“文革”中,戴高帽游行、批斗,住“牛棚”,发到“干校”,这些典型经历钱谷融一件都没有落下。钱谷融一生保持着不做官的态度,建国后硬是当了38年的讲师。据说1979年,钱谷融先生应邀到河南讲学,当主持人宣布“欢迎钱教授演讲”,全场爆发雷鸣般的掌声,这时只见钱谷融站起来面带歉意地说道:“对不起,我是讲师,不是教授。”而他当时,已经是全国著名学者,第一批研究生导师,治学成就举世公认。
钱谷融的性格,从上述细节中可见一斑。钱谷融常常挂在嘴边的话是,做学问和做人一样,第一要正直,第二要诚恳,做人不能弄虚作假,读书尤其不该弄虚作假。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坚守上述信条的钱谷融遭受那些不应有的待遇,自然可想而知。钱谷融的难得,在于对这些信条全身心地坚持,自始至终地坚持,身家性命危在旦夕而不改,金钱利益环绕诱惑而不动,名利荣誉争逐喧嚣而不摇。
钱谷融最喜欢的一本书是《世说新语》,喜欢得久了,钱谷融身上也有一种名士风度——潇洒、从容、真情、质朴。这种风度,既是历经岁月沧桑笑看云卷云舒之后的那份豪华落尽见真淳,也是听从良知良能竹杖芒鞋任凭风和雨的那种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也正因此,钱谷融的“文学是人学”说其实并不深奥,他自己也说,这是从高尔基而来,原本只是常识。但钱谷融的“人学”说,却因为他自身对人的感情、人的需求、人的性灵、人的积淀的高度关注,而具备了别样的一种风味。事实上,我们仰望和羡慕钱谷融的,不是进取事功“人学”中摩顶放踵的铮铮铁骨,而是保守性情“人学”中雍容冲淡的仙风道骨。
在充满了追赶超越,充满了种种规划的今天,连人生、学问甚至感情都似乎可以按部就班地快速前进的今天,钱谷融的冲淡真诚的人生境界,至情至性的美学观点,自然有了一种濒临绝种的诱惑力,引发人们的种种追思和怀念。这种怀念和留恋,诏示着坚守本性、听从本心、随遇而安、以诚动物的永恒价值和时代意义,更揭示了现代性之下人为物役、身心不一、自欺欺人的种种荒谬和不安。
“光风霁月”是钱谷融常常赞许的一个人生境界,其实也正是钱谷融的夫子自道。光风霁月的内里,是圣贤君子超乎寻常的人生格局和价值定力。这种格局和定力,能够让人在逆境时足以遁世无闷、独立不惧,在顺境时自知自觉、心如明镜,在平境时,则有守有为,可止可行,呈现出令国人古今神往的“光风霁月”气象。